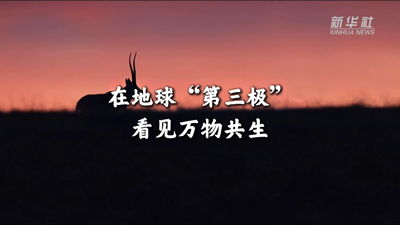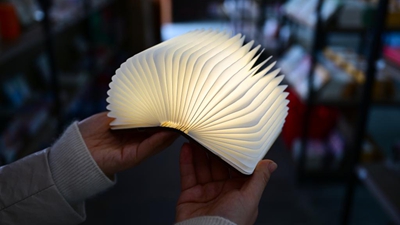新华社成都8月16日电(记者高萌、马思嘉、许仕豪)成都世运会上,许多“兼职”选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世运会项目大多是非奥和小众项目,商业化程度低,绝大部分选手无法以此谋生,因此通常拥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运动员才是“兼职”。
虽然也是运动员,但他们与网球等职业运动中的职业运动员、奥运会上的国家队专业运动员,有很大区别。
他们往往因爱好某项运动而加入俱乐部或社群,并通过赛事体系逐步走上世运会的舞台。
前体操名将商春松在成都世运会收获跑酷女子自由式项目金牌。她在读大学期间接触到了跑酷运动。起初,尽管面临经济压力,她还是在俱乐部报名一对一课程,通过兼职供养自己和这项爱好。不过,随着在国内外赛事中获奖,如今已不存在训练场地和经费困难。
都是搞体育,但练体操和玩跑酷大相径庭。一个有完善的国家体系保障,一个则什么都要自己操心。
从“奥运”到“非奥”的转身,让商春松体会到了专业竞技的“象牙塔”与民间小众运动的“温差”。但她收获同样巨大:“跑酷更强调风格和自由创意,而且让我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有做IT的,有地铁司机。跑酷让我接触到了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世界。”
自嘲是“野生派炭系女孩”的冯浩霖是中国腰旗橄榄球队的四分卫。2021年,因同事介绍而接触到橄榄球的她逐渐成为北京Avengers(复仇者)腰旗橄榄球俱乐部的四分卫,并最终入选国家队。
冯浩霖说,俱乐部就是围绕腰旗橄榄球的培训和参赛来运营,等同于一支队伍,“大家都在‘为爱发电’。发现身边永远有一帮目标一致的人在一起,感觉很安心”。
对于许多像冯浩霖这样的“兼职”运动员,如何保证日常训练与参赛?社会俱乐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团队飞盘赛场上的李雪与周安琪,既是国家队队友也是上海同一家飞盘俱乐部的成员。每周,俱乐部会进行2-3次训练,周中一次周末一次。两人基本没有休闲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在训练比赛。她们所属的沪蛙俱乐部是中国最早一批飞盘俱乐部之一。
李雪对于“俱乐部+联赛”的体系有着自己的观察:“美国飞盘发展比较好,学校有社团,社会有俱乐部,还有职业联赛,形成相对健全的体系,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走。高水平联赛确保了比赛强度,提升了竞技水平。”
活跃在赛场上的不仅仅有俱乐部成员,许多俱乐部运营者,也深度参与着本届世运会。

32岁的岳翰此次参加了男子尾波滑水项目。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接触了尾波滑水,练习约半年就在全美大学生联赛上拿到新人组第二名。2019年回国后,他与好友在杭州创办了一家尾波俱乐部并担任教练。如今,俱乐部有50名稳定会员,并通过进校园、训练营等方式发展青少年爱好者。
他注意到,国内滑水俱乐部数量越来越多,且更多青少年群体加入其中,并在训练后积极参加国内外的业余赛事,不断提升这项运动的覆盖面和专业性。“俱乐部会像星星之火一样,辐射到更多人群。”
出没在自由潜赛场的赵磊是中国第一位AIDA自由潜教练,随后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自由潜俱乐部。目前,该俱乐部已培养出上万名潜水员,其中包括200多名自由潜教练。
“自由潜的运动员没有体制内的保障,他们都是靠热爱在坚持。”赵磊说。他如今仍需在经营俱乐部与培训国家队选手之间寻找平衡。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鲍明晓预测道:“未来我国体育发展的趋势可能要更多地从‘争光体育’转型到‘民生体育’,把体育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融入老百姓对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去。”
而俱乐部,正是其中一种“轴承”。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运动一部部长王鼎在谈及我国壁球发展时表示:“在社会俱乐部层面,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内已有超过100家具备一定规模的壁球俱乐部,他们在商业运营、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为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传统举国体制聚焦“奥运争光”目标;而在小众、新兴项目的赛道,社会俱乐部则从兴趣爱好和群众需求入手,以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构建起了从“全民健身”上升到“竞技体育”的另一条路径。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四部主任刘青说:“尾波冲浪项目在2020-2022年期间得到大力发展,全国开展滑水运动的俱乐部数量激增,巅峰时期超300家俱乐部。借助此风潮,滑水项目在国内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吸引了一批群众参与滑水项目。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对‘造浪机’等体育设施的需求也明显提升,带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从商春松的跑酷转型到冯浩霖的腰旗橄榄球之路,从团队飞盘的国家队选拔到尾波滑水创业者岳翰走上世运会,“兼职”运动员们用自己的方式注解着“运动无限,气象万千”;而他们背后的俱乐部,不仅为爱好者提供了专业训练平台,也通过社群运营、赛事孵化、人才输送,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体育生态。
中国体育的多元发展格局正在这些毛细血管般的组织中被重新塑造。